早上6点,江阳区黄舣镇弥陀渡口。进入汛期,长江水微涨。船长宋久才和同事们登上江阳103号渡船,仔细检查发动机、仪器仪表、救生设备……宋久才一边将硕大的舵盘擦得锃亮,一边往岸上瞧。两位打着伞、背着背篼的乘客正朝码头走来。
这天是5月16日,农历四月十九,正逢黄舣镇弥陀赶场,平时7:30首发的轮渡提前到了6:30。首班乘客只有年过七旬的王光明、郑信秀、李应珍三人。
弥陀、神臂城(也称“老泸州”)渡口,是长江泸州航道上最后仍在运行的渡口,连接着江阳区黄舣镇来龙山村与对岸的合江县神臂城镇老泸村和经盘村。从弥陀渡口到对岸的神臂城渡口大约1.2公里的水路,装载乘客的轮渡往返两岸,从清晨到黄昏,每天至少“跑”8个来回16趟。除了大雾天或涨水天封航,日日如此。

江阳103号渡船停靠在合江县神臂城镇神臂城码头,等待村民上下船。
从青丝到白发
6:15,见王光明和郑信秀上船,水手张春梅热情地招呼:“郑嬢嬢,今天来得有点早哦。”
“我回去看看地里的红苕、苞谷长得好不好,一会儿还要回黄舣接孙孙放学。”落座后,头发花白的郑信秀打开了话匣子。
王光明、郑信秀夫妇是神臂城镇老泸村人。“我嫁到‘老泸州’50多年了,过河船也坐了50多年。”郑信秀说,四五十年前的弥陀渡口很大,每逢赶场天,大家争前恐后过河到弥陀赶场,散场后也是一窝蜂往码头跑,热闹得很。
在郑信秀的心里,弥陀——神臂城渡口和家一样重要。早些年,他们挑娃儿菜、大头菜坐船到弥陀卖,几分钱一斤,一挑菜卖几元钱,是家里一笔不小的收入;后来,孩子长大了在弥陀、泸州读书,坐船来来回回;现在,儿女在黄舣镇安家、工作,老两口每隔三五天就在“老泸州”、黄舣两头跑,送完孙孙上学回老家种地……

江阳103号渡船载着过江赶场的村民。他们带的背篼大小不一,有的装着几只鲜活的土鸭土鸡;有的空空如也,准备采购物品。
王光明已记不清一年要坐多少回过河船。他从几岁第一次出远门到结婚,再到现在白发苍苍,六七十年过去了,大小木船、机动船都坐过,船票从2分、3分、5分、一角、五角、一元到两元。在他看来,渡口似乎变了又没变,变的是渡口和船越来越好,没变的是一直都可以从这里回家……
郑信秀夫妇的龙门阵还没摆完,船已平稳停靠在神臂城渡口。“下午又见。”郑信秀和张春梅道别后,急急忙忙上岸。
此时,岸边已排起了队。“今天雨大、路滑,大家慢点。”水手傅应春跳下船,一边维护秩序,一边拉紧缆绳。村民们背着背篼,有序上船。“大家穿好救生衣,坐好哦,船马上要开了。”张春梅时不时提醒。

江阳103号渡船工作人员见村民搬运货物不便,主动伸出援手,确保下船安全。
这一趟装了26名乘客,绝大多数是中老年人,卖鸡的、卖蛋的、提着塑料桶去打酒的……“村里公交车停运了,我们老年人坐船到弥陀赶场方便点。今天本打算捉两只鸡去弥陀卖,但是下雨不好捉,只能空手去赶场了。”老泸村六组的村民王德云说,最近农忙,赶场多买点日用品。同村村民余明背了两只大公鸡,熟人问他:“你咋不到神臂城去卖呢?那边说不定好卖点。”余明笑了笑说:“去那边要走一个半小时的路,到弥陀就半个小时,方便得多。”
事实证明,余明的选择是正确的。当天7:20,记者在弥陀渡口的趸船上,又一次见到余明。“刚到场上,两只鸡就被同一个顾客买走了,25元一斤,价都没讲。”余明很高兴,卖完鸡坐7:30的船回家,不耽误干农活。
……
一年四季,长江江水涨涨落落。乘客们或走走亲戚,或卖卖农副产品,或买买生活用品,或到附近的园区上班,或外出求学……从青丝到白发,日复一日,彼此熟悉。和滔滔江水一样延绵不绝的,是两岸村民平淡幸福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希望和向往。
从此岸到彼岸
7:30,水手傅应春扬臂将缆绳抛出,汽笛一声长鸣,江阳103号渡船缓缓驶离弥陀渡口,又开始新一趟的往返。
十多分钟后,江阳103号渡船从神臂城渡口接上16名乘客,稳稳驶回起点。驾驶舱中,60岁的船长宋久才将舵盘转得飞起,发动机的操纵杆一前一后,以不同的扭力拉扯着船头转向,精确地向着趸船贴了过去,几乎没有修正。乘客跨一小步,就能下船。

宋久才熟练地操控着江阳103号渡船,从江阳区黄舣镇弥陀码头缓缓启航,朝着对岸合江县神臂城镇神臂城码头驶去,接送村民出行。
这是“老船长”宋久才的真功夫。宋久才到底有多“老”?从16岁那年跟着父亲开渡船算起,他在渡口工作了44年;江阳103号渡船有10名员工,他的工龄最长;“脚蹬鹅宝手刨沙,拼死拼活把船拉”,从撑船到开船,从小木船到机动船,他都经历过。
在宋久才的记忆中,以前,逢年过节、赶场天的早晨和傍晚是最忙碌的,两岸排起长队。船在江中行驶,就能看见岸边翘首以盼的人群,神臂城那岸,等候乘船的人从码头排到了神臂城的城墙。那时候船小,只要挤得下就上。船舷外,水触手可及,遇到调皮的孩子,稍有不慎就有落水的危险。遇到涨水天,船在激流中随波逐流,有时还偏离航线。有一年涨水季,枯枝树叶等混作一团冲袭而来,船被撞得摇摇晃晃。这时,最考验船长和水手们的应对能力了。宋久才和同事们一边奋力摇桨,一边提醒大家“站好,不要动”,以防乘客在慌乱中走动造成船体晃动甚至倾斜。
每次起航前,宋久才都要拿起无线电高频设备,向上下游几公里水域航行的船只发出信号。以前,过江轮渡在开航前,船员要用望远镜观察过往船只,通报船位、动向等信息,确保船只安全。开航前鸣笛,表示准备移泊,用不同声号的鸣笛表示不同的含义。“有了高频设备,安全系数增加了。”宋久才说。

江阳103号渡船驶向合江县神臂城镇神臂城码头。
2003年,江阳103号渡船投用,最大核载75人。大船安全,操作起来轻松。然而,酷暑高温天,仅一平方米的驾驶室里,太阳直射,宋久才大汗淋漓,双手在发烫的舵盘上操作,火辣辣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甲板被晒得滚烫,船舱内的温度最高时五十多摄氏度,像蒸笼一样,所有员工仍寸步不离船。
以前,两岸村民结婚、过生日、升学等大事喜事,经常包船过河,热闹又喜庆。逢年过节,一天上千人次乘船是常态。随着神臂城长江大桥通车和私家车增多,坐船的人越来越少,平均每天客流量两百多人次。“5到9月是渡口的淡季,逢场天有上百人次坐船,平时一天就几十人次。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渡船作为公益项目运转着。”江阳103号渡船所属的江阳轮船公司经理周忠正说。
周忠正在弥陀渡口工作了25年,对渡口的历史比其他人更了解:宋元之际,这里是水军的作战基地。大米、茶叶、蔬菜等在这里交易、中转,商贾云集、往来船只如梭,成为出行的必经之路和物资集散地。

江阳103号渡船驶向合江县神臂城镇神臂城码头。
如今,曾经每逢赶场天上千人次乘船的繁华和热闹一去不返,但船上的每个人都在坚守“。那些年坐船的大姑娘小伙子,有的已白发苍苍;坐船上学的孩子,早已远走他乡……”周忠正说,岁月轮回,渡船仍在原地接送村民,一程又一程。
17:30,江阳103号渡船准时启程,履行当天最后一趟使命。很快,江面上留下一道水痕……
这是长江泸州段航道最后一条过江轮渡。宋久才和同事们每天依然往返江上,目送乘客上船下船,从此岸渡到彼岸,从清晨到黄昏。
(来源:泸州市融媒体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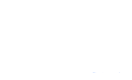




评论 0
还没有添加任何评论,快去APP中抢沙发吧!